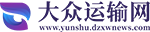近日,上海龙美术馆(西岸馆)推出了十周年系列展之“龙与士——明代中国书法和绘画艺术特展”。
在八十余件书画文物中有一件明代画家周臣的作品颇为引人关注。周臣的名字在画史上或许算不上闪耀,但他的艺术探索对其学生唐伯虎与仇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雅与俗交融
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走进龙美术馆“龙与士——明代中国书法和绘画艺术特展”的展厅,一幅气势高远、画风精美的《观潮图》呈现于展厅的显著位置。
策展人谢晓冬告诉记者,画中描绘的是文人临轩观潮的壮阔情景,作品采用对角线构图,山势高峻、石骨坚致,斧劈兼刮铁的皴法取自南宋大画家马远的画法,严谨雄劲又流利清逸。
《观潮图》的作者是明代画家周臣。周臣号东村,是今苏州人,他一生漫长的绘画生涯见证了明成化至嘉靖年间的社会文化之变。
明朝初年,朱元璋为复兴汉文化,在书画等方面大力提倡恢复宋风。宋代宫廷有画院,明代也设立各种宫廷美术创作机构。书画收藏界至今有一种说法:明初的院体画与宋画很难分辨,因为明初的画师基本都在学宋画。他们学的最多的就是马远、夏圭、李唐、刘松年,即“南宋四家”,由他们所代表的山水画派在美术史上被称为“院体”。院体山水在画法上以水墨苍劲的大斧劈皴为特色,在取景上以局部特写的边角之景为特点,以细节的真实构成清新的意境。
作为活跃于苏州画坛的职业画家,周臣对当时流行的宋代院体画颇有研究,他的笔墨技法是典型的南宋院体风格,乍一看很像马远或刘松年的作品。明代戏曲理论家何良俊在《四友斋丛说》中这样评价周臣:“其画法宋人,学马夏者若与戴静庵(进)并驱,则互有所长。未知其果孰先也,亦是院体中一高手。”意思是周臣与当时浙派的代表人物、有“第一国手”之称的戴进可谓并驾齐驱。
到了明代中期,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投入绘画创作,画坛开始追求元人悠然淡逸的画风,向往自由灵性的画境,吴门画派逐渐崛起。周臣的绘画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,他逐渐吸收了文人画的特点,力求雅与俗相交融,在山水画的图式和技法上形成了个人的特色。
画中有诗意
关于周臣的艺术成就曾有两种不同的声音。喜欢他的人认为,他的作品如美玉一般珍贵。有人则认为他更像一位画匠,离文人画推崇的“逸笔草草,不求形似”的境界尚有一定的距离。从周臣留存至今的作品来看,他是一位融入了文人画气质的院派传人,兼顾了笔墨技法与文人情怀,用院体画技法表达文人雅逸,在传统中注入个人情感。
《北溟图》有《观潮图》的“姊妹篇”之称,因为两幅作品都描绘了文人观海、向往自由洒脱的意境。《北溟图》取自庄子的《逍遥游》,画面中一位文人正倚在阁楼的窗上平静地看着海潮翻涌,波涛汹涌的大海与其身处的安详静谧的村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静与动、实与虚的交织,表现了冲破桎梏、拥抱自由的理想。
周臣非常擅长从诗文、典籍中寻找灵感,这使得他的画面具有一定的可读性。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《柴门送客图》是周臣的代表作之一,他以杜甫《南邻》中的“相对柴门月色新”入画,主人送客出门时已是新月高挂时分,船工正在船头酣睡,可见主客相聚甚欢忘记了时间。这幅画的用笔是典型的浙派风格,斧劈皴、钉头皴与披麻皴交替参用,刚柔相济,用墨一笔到底,浓淡自然而生,可谓周臣将院体画与文人画的表现方式相融的典型之作。
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闲看儿童捉柳花》是周臣根据宋代杨万里的《闲居初夏午睡起·其一》绘制的。诗曰:“梅子留酸软齿牙,芭蕉分绿与窗纱。日长睡起无情思,闲看儿童捉柳花。”画中描绘了暮春时节,午睡后的高士悠闲地散步在庭院里看孩童玩耍的情趣。
天津博物馆收藏的《香山九老图》也是周臣的一幅佳作。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晚年退居香山,与胡杲、刘真、郑据、张浑等人被并称为“香山九老”,他们远离世俗,忘情山水,耽于清淡。此作的画面布局饱满,结构精整,人物神态各异,生动自然。记录的是一种悠闲自得的生活方式,也是古代文人雅士追求隐逸的写照。
《流民图》是周臣非常独特的作品,可以说是明朝乃至中国古代绘画史中少有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。周臣用写实手法描绘了明朝正德年间政治腐败、朝政荒废导致难民流亡、民生凋敝的悲惨景象,发人深省。
青出于蓝
周臣之所以被认为是明代美术史上的关键人物,关键还在于他对“吴门四家”中的唐寅与仇英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在“龙与士——明代中国书法和绘画艺术特展”展出的诸多作品中,有两件难得的唐寅书画作品《金阊送别图》《行书七古诗卷》,以及仇英的画作《人物图卷》,可谓师徒三人共同亮相。
周臣是唐寅的启蒙老师。据传,唐寅从小顽劣,学画时经常调皮地去捉螃蟹。周臣见状,便用自己画的螃蟹与唐寅抓的活螃蟹比试,以此来启迪唐寅。在周臣的悉心培养下,唐寅踏踏实实地学习了精工的院体山水画法。见唐寅在山水、人物、竹子等方面已颇有造诣,周臣又把唐寅推荐到沈周门下学习。
如果将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唐寅的《草堂话旧图》与周臣的《怡竹图》相比,不难看出唐寅的画作深受周臣范式的影响。两人草堂的画法基本一致,但唐寅减去了围栏与廊柱,堂中是对谈的文人而不是主人与童仆,又消减了近处的山石和松树,给草堂之后的山岳留出了表现空间。画面既不冗杂无序,也不逼仄拥挤,精致细腻而无匠气。比起周臣的作品,唐寅在技法、立意与内涵上都做到了全面的超越。
仇英出身寒微,早年当过漆匠,周臣见仇英很有绘画天赋又谦逊好学,便收他为徒。在周臣的指导下,仇英遍临唐宋名作而臻于极致,深得院体理法,最终成为青绿山水大家,后世董其昌感叹:“五百年而有仇实父。”
关于师徒三人的画技,曾有史家评论称:“六如秀润而超逸,东村工密而苍老,实父工密有余,苍老不足,无望超逸。”若以文人画追求的“超逸”为标准,那唐寅的艺术境界可谓三人中最佳,甚至超越了他的老师。尽管师徒三人各有千秋,但唐寅和仇英无疑都继承并发展了周臣的艺术特色,将院体画与文人画相融汇,为中国绘画开拓了新的局面。